读《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徽州丝绢案始末》有感
文章讲述了帅嘉谟因发现人丁丝绢之不妥,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在阅读过程中,看见各县言官言辞之犀利,看见各级官员之人情世故,看见马亲王以以小见大的方式切入历史之清晰。还看见了这个历史类纪实性质的故事里面,似乎有着几分局的影子。
顺着故事主线,从帅嘉谟发觉有纰漏,查阅典籍:此前已有两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曾两次越级上报,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而自己的第三次呈文,似乎也要以不了了之收场。却在万历三年(四年之后)被高速推动了起来。
再看故事结果,歙县少缴2530两;五县吃了个暗亏,但目前没啥变化;对朝廷来说,一则税收并无短少,二则对新制的推行是件好事。算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整个故事颇有投石击水的味道,也有着三仙献鼎的影子。
首辅想要推行新政,哪里受到的阻力最大?必然是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的群体——乡绅、乡宦。如何消除阻力?皇权。但在帝制时期,却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皇权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管理。如何让“皇权下县”?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
于是,沉寂四年的绢丝案,得到了高速的推动。
而故事的主角帅嘉谟,似乎也和局中描写的傀儡结局差不多:以“谁让你多事”罪“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若是用三仙献鼎来剖析故事,少不了谈到“千门八将,少五不做局”。除了作为正将的首辅外,剩余的几将都是由什么角色来扮演的?
火将自然是兵备道了;乡绅们的书信、言官们的状书,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贴、告示、奏文倒是很好的充当了除、风两将;而最为关键的反将,正好是绢丝案本身。
走进三仙献鼎,把目光放在婺源,貌似在上演着一幕鹃生永逸;最后把目光聚焦于程任卿,他却也好像正在扮演断路修罗。
最后不得不再感慨,马亲王笔下的显微镜,能见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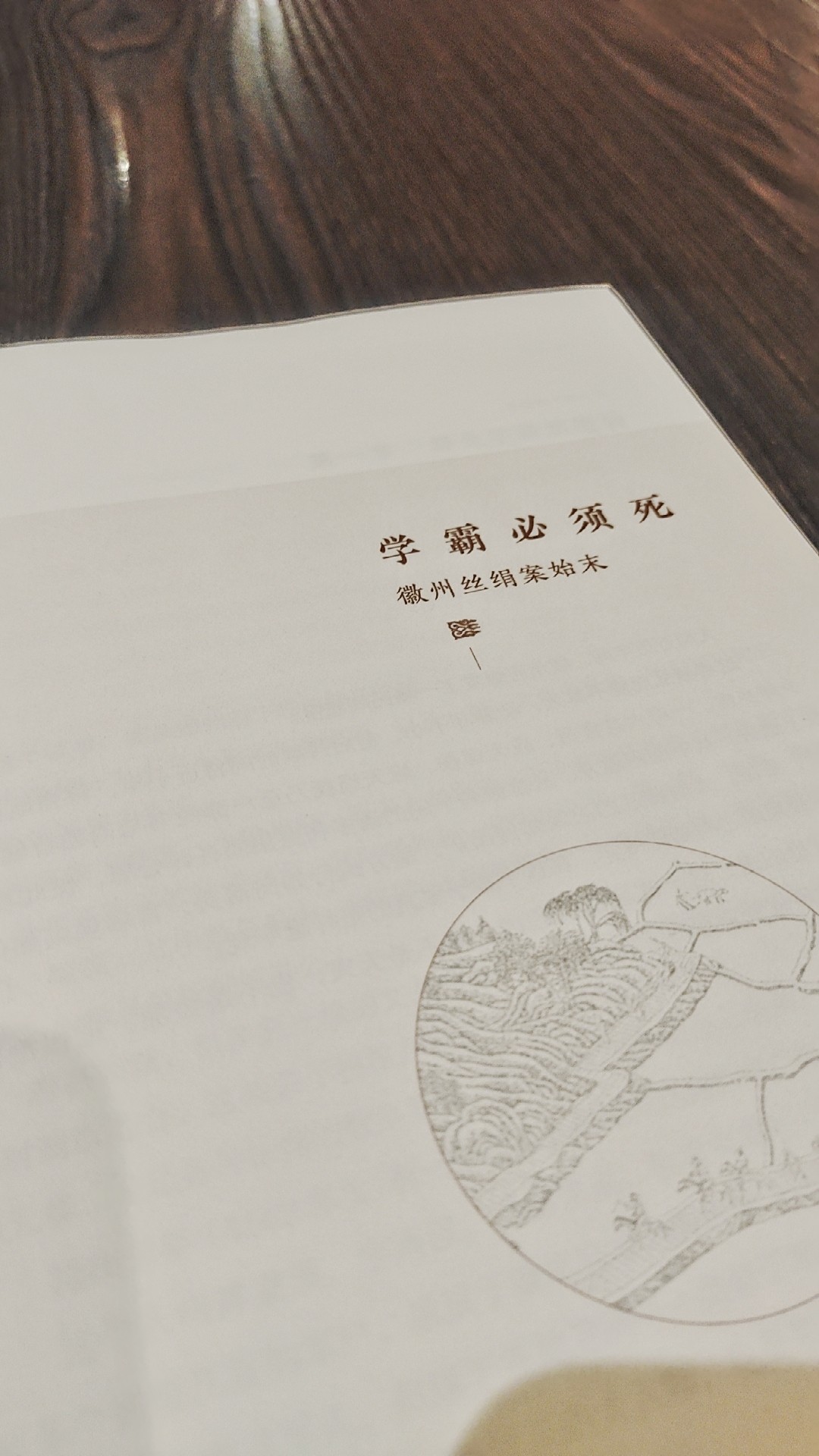
评论:
热爱学习的宝藏男孩: 欢迎互关做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