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很忙,无聊中将张岱的生平看了看,文章名句大致浏览了一下,认真阅读了他对《陶庵梦忆》所作的序言,心中无味杂陈,不知怎么表述。 和曹雪芹相比,张岱可能更幸运些,“繁华靡丽”基本都在中青年的时候,可谓是享尽了美好滋味;但又是很不幸的,因为有着国破家亡的那种“恨”。至于其中的真切,我并不能感同身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繁华,艰难求生已是不易,可能能让张岱的“黄粱梦”和“南柯梦”成真,他很想再回到过去,回到那个鲜衣怒马的时期。而我,之前在阅览西塞罗《论老年》的时候说过,假如有重活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拒绝的。并非悲观,而是自出生以来,不过就是按部就班的活着,没有“湖心亭赏雪”,也没有研制“兰雪茶”的雅兴之机,更没有“金山夜戏”的热闹与大胆。总之,就是平平淡淡,和大多数人一样。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读了哲学,使我在身体的按部就班中,思想能够超脱出来审视一下自己。不过,我的周围和环境一直告诉我,生活需要的不是哲学,哲学与当下平凡求生的生活格格不入,需要的是按照社会规则去“努力”,以期望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生活条件。至于思想,生活不需要,这个社会也不需要。可能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唯一一次“例外”——对哲学的向往,其它的和芸芸众生一样,出生、长大、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子、养育、退休、死去,然后黄土覆盖,不留痕迹。 说一句纯属戏谑的话,我觉得张岱的经历虽说精彩,但不如“我、我们”那样的“精彩”,他没有经历过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无休止的“单一性的生活”,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又和今天一样的氛围。我真怕他在这种“单一性”的生活中提前“引决”。我很有幸,和这么的多人,经历着工业社会中那种“单一性”的“精彩”。如果能够充分发动思想的力度,在这种“单一性”中所领悟到的东西,比张岱更为深刻、更为悲壮。至少张岱和曹雪芹还有梦做,“单一性”成长起来的我们,到哪里去寻梦?那些梦都是别人的和社会的,都是资本的。 我现在还很年轻,不过余生的路也已经想好了,做一个“懂自己的心、做自己的事”的普通人,一方面运用好社会规则,多挣点,争取过得好一点;另一方面,建立私人“图书馆”,遍览群书,潜心积累,用思想贯彻灵魂,使灵魂始终处于“充盈状态”,以期与“单一性”形成抗衡局面,在这种相对平衡中,度过余生。张岱写《陶庵梦忆》是为了一个“名”,想要流芳百世,他是有这个资格。我写文章,什么也不图,就图在每个风雨交加的雨夜,能够安稳的睡去,我也有这个资格。 一个问题:是繁华靡丽散尽,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感叹人生如梦悲壮?还是在“单一性”中坚定的活着,力争在其中鼓捣出不一样的“精彩”更为壮烈呢?我选择后者,我只能是后者。 2022年10月14日16:2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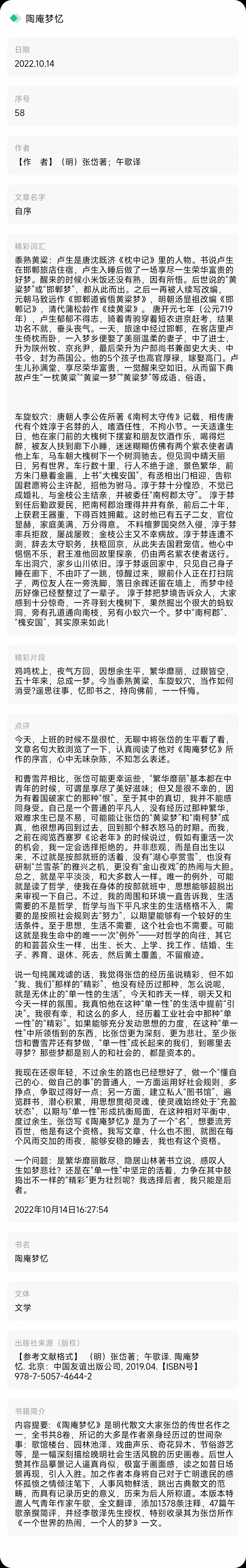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