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而言,一个人始终是一个人,是某个最先的和最终的和异常惊人的东西,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种类,没有什么总数,也没有归零一说。不管他的杜撰和估价是多么愚昧和狂热,不管他多么严重地误解了自然的进程,否认了自然的条件:——所有的伦理学从来都是极其愚昧和反自然的……每当那“英雄”登上舞台,都会获得某种新鲜货色,骇人听闻的笑的反面,大量个体的那种深度震颤,因了这样一个想法:“是的,活着是值得的!是的,我是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我和你,我们所有人,在某些时候又一次让我们产生了兴趣。——不可否认的是,长时间地,笑、理性和自然一直都主宰了这些伟大的目的导师当中的每个个体:短暂的悲剧最后总是转向和回到永恒的此在之喜剧,还有,“无数大笑的浪潮”——用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最后必定也会扫荡这些悲剧人物中最伟大者。然而,在所有这些矫正性的笑声中,整体说来,通过那些此在之目的的导师的层出不穷的涌现,人类的自然本性已经被改变了,——它现在多了一种需要,就是需要此类导师和有关“目的”的学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人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幻想的动物,必须比其他任何动物更多地满足一个生存条件,即:人必须时而相信自己知道为何而生存,要是没有一种周期性的对于生命的信赖,要是没有对生命中的理性的信仰,则人的种类就不可能繁荣昌盛!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一部(第1—56节)
1 》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在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一切束缚他的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其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着我的灵魂。
——李银河《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开篇 我的心路历程.二、为什么》
我的主要焦虑就是:什么事是我真正愿意去做的。我喜欢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抱一本书(必须是好看的书),感受人类最美好的灵魂创造出来的智慧和美;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看真正的好电影;我还喜欢写一点东西,但必须是有趣的,是真情实感。有时,我还有一点辩论的冲动,那是当我看到有些事过于荒谬时。有时,我还有一点点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别人是怎么过的,怎么想的——这就是社会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当太阳在外面凶猛地照射时,当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时,能够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来。这种感觉十分惬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了。
——李银河《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开篇 我的心路历程.三、享受人生》
生存的目的是对美的享用。换句话说,为生存的劳作只是手段,而目的是审美,是从对美和艺术品的欣赏中得到生存的愉悦感。
艺术家的生存方式,是更加纯粹的审美生存,因为就连他的劳作都是审美。创造美的艺术品是他的生存方式。
——李银河《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只有审美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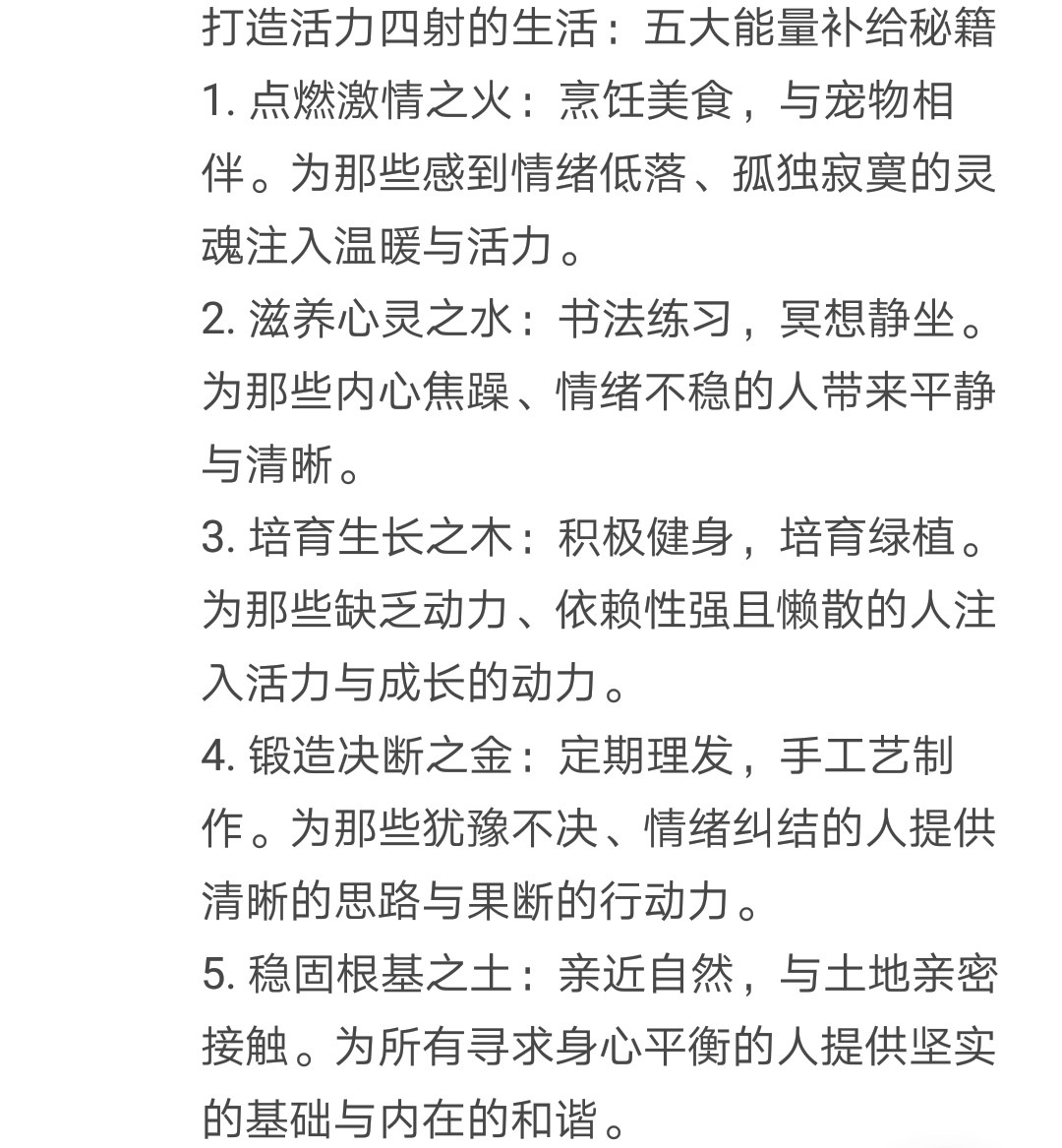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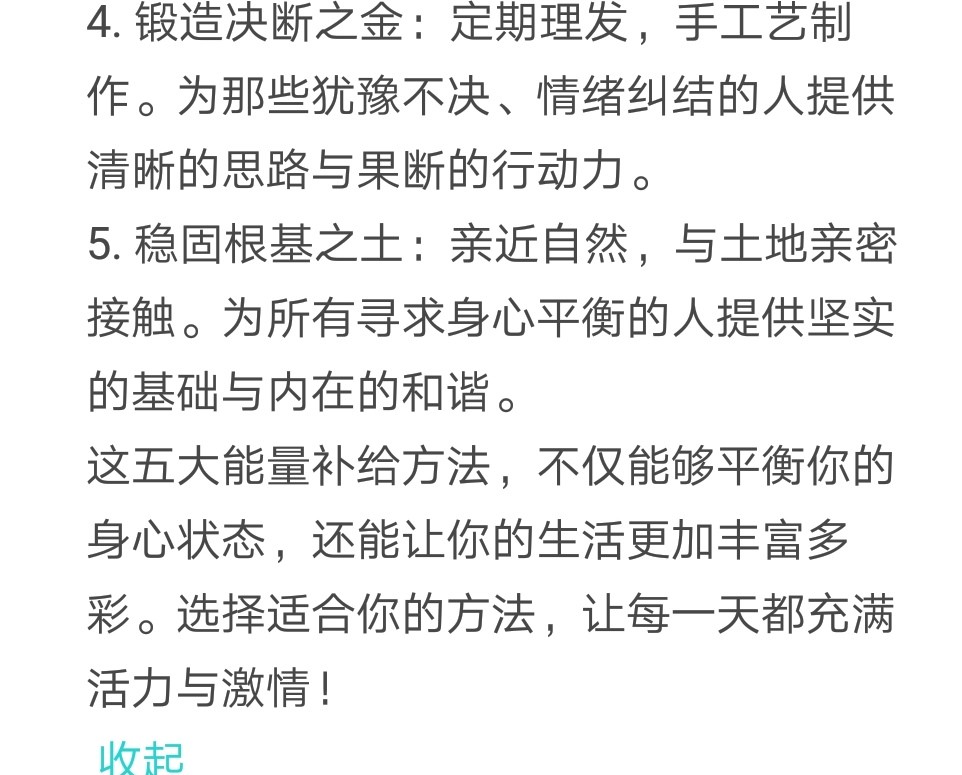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