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ҠӘеҠӣз§ҚиҠұпјҢиқҙиқ¶иҮӘ然дјҡжқҘпјҢжңҖеқҸд№ҹжӢҘжңүдёҖзүҮйЈҺжҷҜгҖӮ 1978е№ҙпјҢеҮҖиә«й«ҳ175пјҢдҪ“йҮҚ65гҖӮеңЁеҸҢжөҒеҒҡе·ҘеҺӮиҝҗиҗҘпјҢж•°еӯ—еҢ–жҺЁе№ҝдё»з®ЎгҖӮеҚ•иә«12е№ҙпјҢеқҗж ҮжҲҗйғҪйҫҷжіүпјҢиҝҳиғҪжүҫеҲ°и°Ҳеҫ—жқҘзҡ„еҗ—пјҹдёӘдәәй•ҝзӣёзӣ®жөӢ35~38еІҒгҖӮ 科зҸӯжңәжў°жҠҖжңҜжңҚеҠЎпјҢд»ЈзҗҶе•Ҷз®ЎзҗҶпјҢдёҡдҪҷзҲұеҘҪж•°жҚ®еӨ„зҗҶгҖӮиЎҢдёҡдёҚжҷҜж°”пјҢ45еІҒиҪ¬иЎҢеҒҡж•°жҚ®еӨ„зҗҶпјҢе·ҘеҺӮж•°еӯ—еҢ–жҺЁе№ҝгҖӮ >>йҳ…иҜ»жӣҙеӨҡ
1978е№ҙеӨ§еҸ”第25ж¬ЎзӣёдәІпјҡгҖҠиӣӢзі•зҡ„и§үжӮҹгҖӢ жҲ‘еҗ‘жқҘжҳҜдёҚжғ®д»ҘжңҖеқҸзҡ„жҒ¶ж„ҸжқҘжҸЈжөӢдәәзҡ„пјҢ然иҖҢд»Ҡж—Ҙд№ӢдәӢпјҢеҚҙд»ҚдҪҝжҲ‘иёҢиәҮиүҜд№…гҖӮ еӨҸе°Ҹе§җпјҢе№ҙйҖҫдёүеҚҒпјҢеҚҙд»Қиў«е”ӨдҪңвҖңе°Ҹе§җе§җвҖқпјҢд»ҝдҪӣеІҒжңҲеңЁеҘ№иә«дёҠеӨұдәҶж•ҲгҖӮзӣёиҜҶеҚҠжңҲпјҢиЁҖи°Ҳз”ҡж¬ўпјҢжҒ°йҖўеҘ№з”ҹиҫ°пјҢдҫҝи®ўдәҶдёҖзӣ’иӣӢзі•пјҢиҒҠиЎЁеҝғж„ҸгҖӮ иӣӢзі•жҳҜжүҳеӨ–еҚ–е°Ҹе“ҘйҖҒзҡ„гҖӮжҲ‘й©ҫиҪҰиҪҪеҘ№еҮәй—ЁпјҢеңЁжҲҗйғҪжҙӘе®Ғдёүи·Ҝ1399еҸ·пјҢзүҷиҙқеә·еҸЈи…”пјҢжӯЈе·§йҒҮдёҠйӮЈйҖҒиӣӢзі•зҡ„е°Ҹе“ҘгҖӮд»–дёҖиә«й»„иЎЈпјҢйқўиүІй»қй»‘пјҢйўқдёҠжІҒзқҖжұ—зҸ пјҢжҳҫ然жҳҜиө¶и·ҜеҢҶеҝҷгҖӮеӨҸе°Ҹе§җжҺҘиҝҮиӣӢзі•пјҢдёҚзҹҘжҳҜжүӢж»‘иҝҳжҳҜеҝғдёҚеңЁз„үпјҢйӮЈзӣ’еӯҗз«ҹд»ҺеҘ№жүӢдёӯж»‘иҗҪпјҢвҖңе•ӘвҖқең°дёҖеЈ°ж‘”еңЁең°дёҠпјҢеҘ¶жІ№еӣӣжәўпјҢиӣӢзі•еЎҢйҷ·пјҢжҙ»еғҸдёҖеј иў«иё©жүҒзҡ„и„ёгҖӮ вҖңдҪ жҖҺд№ҲжӢҝзҡ„пјҹвҖқеӨҸе°Ҹе§җзҷ»ж—¶еҸҳдәҶи„ёиүІпјҢдёҖжҠҠжүҜдҪҸе°Ҹе“Ҙзҡ„иў–еӯҗпјҢвҖңиө”й’ұпјҒвҖқ йӮЈе°Ҹе“ҘжҖ”дҪҸдәҶпјҢеҳҙе”Үзҝ•еҠЁпјҢеҚҙеҗҗдёҚеҮәеҚҠдёӘеӯ—гҖӮд»–зҡ„зңјйҮҢй—ӘиҝҮдёҖдёқжғ¶жҒҗпјҢеғҸжҳҜиў«зҢҺжһӘзһ„еҮҶзҡ„е…”еӯҗгҖӮ жҲ‘еқҗеңЁиҪҰйҮҢпјҢзңӢеҫ—зңҹеҲҮгҖӮиҝҷиӣӢзі•еҲҶжҳҺжҳҜеҘ№иҮӘе·ұеӨұжүӢж»‘иҗҪпјҢеҚҙиҰҒиө–еңЁеҲ«дәәеӨҙдёҠгҖӮжҲ‘жҺЁй—ЁдёӢиҪҰпјҢеӨҸе°Ҹе§җд»ҚеңЁеҺүеЈ°е‘өж–ҘпјҢеЈ°йҹіе°–еҲ©еҰӮеҲҖпјҢеҲ®еҫ—дәәиҖіиҶңз”ҹз–јгҖӮ еӣҙи§Ӯзҡ„дәәжёҗжёҗиҒҡжӢўпјҢдёҫзқҖжүӢжңәпјҢеғҸдёҖзҫӨе—…еҲ°иЎҖи…Ҙзҡ„з§ғ鹫гҖӮжңүдәәзӘғ笑пјҢжңүдәәжҢҮжҢҮзӮ№зӮ№пјҢеҚҙж— дәәдёҠеүҚиҜҙеҸҘе…¬йҒ“иҜқгҖӮ жҲ‘иө°дёҠеүҚпјҢжӢҚдәҶжӢҚе°Ҹе“Ҙзҡ„иӮ©иҶҖпјҡвҖңиӣӢзі•жҳҜжҲ‘и®ўзҡ„пјҢжҲ‘дәІзңјжүҖи§ҒпјҢжҳҜеҘ№иҮӘе·ұжІЎжҺҘдҪҸгҖӮвҖқ еӨҸе°Ҹе§җзҡ„и„ёиүІйңҺж—¶еҸҳдәҶпјҢе…ҲжҳҜж¶ЁзәўпјҢ继иҖҢиҪ¬йқ’пјҢжңҖеҗҺз«ҹжіӣеҮәдёҖеұӮжғЁзҷҪгҖӮеҘ№зһӘзқҖжҲ‘пјҢзңјйҮҢе°„еҮәдёӨжҠҠеҲҖеӯҗпјҡвҖңдҪ вҖҰвҖҰдҪ д»Җд№Ҳж„ҸжҖқпјҹвҖқ жҲ‘жІЎзҗҶдјҡеҘ№пјҢеҸӘеҜ№йӮЈе°Ҹе“ҘйҒ“пјҡвҖңиҝҷдәӢдёҺдҪ ж— е…іпјҢжҲ‘дјҡз»ҷдҪ еҘҪиҜ„гҖӮвҖқ д»–еҰӮи’ҷеӨ§иөҰпјҢиҝһиҝһйһ иә¬пјҢйҖғд№ҹдјјең°йӘ‘дёҠиҪҰиө°дәҶгҖӮ жҲ‘ејҜи…°жӢҫиө·йӮЈеӣўзғӮжіҘдјјзҡ„иӣӢзі•пјҢеҘ¶жІ№жІҫдәҶдёҖжүӢпјҢй»Ҹи…»и…»зҡ„пјҢеғҸжҹҗз§Қз”©дёҚи„ұзҡ„жұЎз§ҪгҖӮжҲ‘иө°еӣһиҪҰеүҚпјҢе°ҶиӣӢзі•жү”иҝӣеһғеңҫжЎ¶пјҢеҸҲжү“ејҖиҪҰй—ЁпјҢеҸ–еҮәеӨҸе°Ҹе§җж”ҫеңЁеә§дҪҚдёҠзҡ„еҢ…е’Ңиҙӯзү©иўӢпјҢж•ҙж•ҙйҪҗйҪҗең°ж‘ҶеңЁи·Ҝиҫ№гҖӮ вҖңдҪ е№Ід»Җд№ҲпјҹвҖқеҘ№з»ҲдәҺеӣһиҝҮзҘһжқҘпјҢеЈ°йҹійҮҢеёҰзқҖйўӨгҖӮ жҲ‘зңӢдәҶеҘ№дёҖзңјгҖӮйҳіе…үз…§еңЁеҘ№зІҫеҝғдҝ®йҘ°зҡ„и„ёдёҠпјҢзІүеә•дёӢзҡ„з»Ҷзә№жӯӨеҲ»ж јеӨ–еҲәзӣ®гҖӮжҲ‘зӘҒ然жғіиө·еҲқи§Ғж—¶пјҢи§үеҫ—еҘ№зңүзңјеҰӮз”»пјҢеҰӮд»ҠзңӢжқҘпјҢйӮЈз”»дёҠз«ҹзҲ¬ж»ЎдәҶиҷұеӯҗгҖӮ вҖңдәәе“ҒжҜ”зҫҺиІҢжӣҙйҮҚиҰҒгҖӮвҖқжҲ‘иҜҙе®ҢпјҢиҪ¬иә«дёҠиҪҰпјҢжү¬й•ҝиҖҢеҺ»гҖӮ еҗҺи§Ҷй•ңйҮҢпјҢеҘ№зҡ„иә«еҪұи¶ҠжқҘи¶Ҡе°ҸпјҢжңҖз»ҲеҢ–дҪңдёҖдёӘй»‘зӮ№пјҢж¶ҲеӨұеңЁиЎ—и§’гҖӮжҲ‘еҝҪ然笑еҮәеЈ°жқҘгҖӮиҝҷиӣӢзі•пјҢжң¬жҳҜиҰҒеәҶзҘқвҖңз”ҹиҫ°еҝ«д№җвҖқзҡ„пјҢеҰӮд»ҠеҖ’жҲҗдәҶвҖңдәӨеҫҖз»Ҳз»“вҖқзҡ„зҘӯе“ҒгҖӮ дё–й—ҙзҡ„з”·еҘід№ӢдәӢпјҢжңүж—¶з«ҹдёҚеҰӮдёҖеқ—ж‘”зғӮзҡ„иӣӢзі•жқҘеҫ—зңҹе®һгҖӮиӣӢзі•зўҺдәҶпјҢиҮіе°‘иҝҳиғҪзңӢи§ҒйҮҢйқўзҡ„йҰ…ж–ҷпјӣдәәеҝғеқҸдәҶпјҢеҚҙжҖ»иҰҒиЈ№зқҖеұӮзі–иЎЈгҖӮ жҲ‘ж‘ҮдёӢиҪҰзӘ—пјҢи®©йЈҺеҗ№ж•ЈиҪҰйҮҢзҡ„йҰҷж°ҙе‘ігҖӮйӮЈйҰҷж°”еҺҹжң¬д»ӨжҲ‘жІүйҶүпјҢеҰӮд»ҠеҚҙеҸӘи§үеҫ—еҲәйј»гҖӮ >>йҳ…иҜ»жӣҙеӨҡ

1978е№ҙеӨ§еҸ”第23ж¬ЎзӣёдәІгҖҠзӣёеҰҮж–°еҪ•гҖӢ
жҲҗйғҪзҡ„еӨ©иүІзҒ°и’ҷи’ҷзҡ„пјҢеғҸжҳҜи’ҷдәҶеұӮжІ№зәёгҖӮеҸӢдәәзЎ¬жӢҪжҲ‘еҺ»зӣёдәІпјҢиҜҙжҳҜвҖңж–°жҙҫеҘіеӯҗвҖқгҖӮжҲ‘жң¬дёҚж„ҝеҺ»пјҢдҪҶеҝөеҸҠ家дёӯиҖҒжҜҚеӨңеӨңеҝөеҸЁвҖңдёҚеӯқжңүдёүвҖқпјҢеҸӘеҫ—еҘ—дёҠжөҶжҙ—еҫ—еҸ‘зЎ¬зҡ„ж јеӯҗиЎ¬иЎ«иөҙзәҰгҖӮйҖ”еҫ„жҙӘе®Ғдёүи·Ҝ1399еҸ·пјҢзүҷиҙқеә·еҸЈи…”пјҢеҮҶеӨҮз”ЁеҚҙеҸҲжІЎз”ЁжҺүжҲ‘зҡ„ж»ЎеҮҸеҲёпјҢжҲ‘зҡ„йҖҒдҪ еҗ§гҖӮ
йӮЈеҘіеӯҗеқҗеңЁе’–е•ЎйҰҶзҡ„зҺ»з’ғ幕еўҷж—ҒпјҢзӣ®жөӢдёүеҚҒеҮәеӨҙзҡ„е№ҙзәӘпјҢеҚҙжҠҠеӨҙеҸ‘жҹ“жҲҗ银зҒ°гҖӮи§ҒжҲ‘иҗҪеә§пјҢзңјзҡ®д№ҹдёҚжҠ¬пјҢеҸӘйЎҫзқҖ用镶钻зҡ„жҢҮз”Іж•ІеҮ»жүӢжңәеұҸ幕гҖӮвҖңзЁӢеәҸзҢҝпјҹвҖқеҘ№еҝҪ然ејҖеҸЈпјҢеҖ’еғҸжҳҜй—®дёӘзү©д»¶гҖӮ
жҲ‘еә”дәҶеЈ°пјҢеҘ№дҫҝдјёеҮәдёүж №жүӢжҢҮпјҡвҖңе№ҙи–Әдә”еҚҒдёҮжҳҜеә•зәҝпјҢдёҚжҺҘеҸ—е’ҢиҖҒдәәеҗҢдҪҸпјҢ家еҠЎжүҫй’ҹзӮ№е·ҘгҖӮвҖқиҜқйҹіжңӘиҗҪпјҢеҸҲиЎҘ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еҪ©зӨјиҰҒдә”еҚҒдёҮзҺ°йҮ‘пјҢе©ҡзӨјиҰҒеңЁеҚҺе°”йҒ“еӨ«еҠһгҖӮвҖқ
жҲ‘жңӣзқҖеҘ№ж–°зә№зҡ„жҹіеҸ¶зңүпјҢеҝҪжғіиө·еүҚж—Ҙдҝ®еӨҚзҡ„ж—§д»Јз ҒгҖӮйӮЈд»Јз Ғд№ҹжҳҜиҝҷиҲ¬пјҢеұӮеұӮеөҢеҘ—зқҖж— зҗҶжқЎд»¶пјҢеҒҸиҝҳиҰҒз”ЁйҺҸйҮ‘жЎҶжһ¶иЈұиө·жқҘгҖӮйӮ»жЎҢеҮ дёӘзҷҪйўҶзӘғзӘғз§ҒиҜӯпјҢеӨ§зәҰеңЁз¬‘жҲ‘еҸҲжҳҜдёӘвҖңиў«жҳҺз Ғж Үд»·зҡ„иҙ§зү©вҖқгҖӮ
вҖңз”ҹиӮІжҚҹдјӨиә«дҪ“гҖӮвҖқеҘ№жҠҝдәҶеҸЈжүӢеҶІе’–е•ЎпјҢвҖңдҪ 们男дәәиҮӘ然дёҚжҮӮгҖӮвҖқжқҜжІҝз•ҷдёӢеҚҠеңҲзҢ©зәўе”ҮеҚ°пјҢеҖ’еғҸеҲӨе®ҳ笔画зҡ„з”ҹжӯ»з°ҝгҖӮжҲ‘жғіиө·иҖҒ家е ӮеұӢйҮҢдҫӣзҡ„зҘ–е®—зүҢдҪҚпјҢйҰҷзҒ«й’ұе°ҡдёҚйңҖиҝҷиҲ¬жҳӮиҙөгҖӮ
зӘ—еӨ–驶иҝҮиҫҶеһғеңҫиҪҰпјҢжӢҫиҚ’иҖҒдәәдҪқеҒ»зқҖиғҢзҝ»жүҫеәҹе“ҒгҖӮеҘ№и№ҷдәҶи№ҷзңүпјҡвҖңжүҖд»ҘиҜҙиҰҒдҪҸй«ҳз«Ҝе°ҸеҢәгҖӮвҖқжүӢжңәеұҸ幕жҳ еңЁеҘ№зһіеӯ”йҮҢпјҢз…§еҮәеҮ еҲҶиҙ§зңҹд»·е®һзҡ„еҶ·й…·вҖ”вҖ”иҝҷе№ҙжңҲпјҢиҝһзӣёдәІйғҪе…ҙиө·дәҶKPIиҖғж ёгҖӮ
жҲ‘ж‘©жҢІзқҖжқҜжІҝпјҢеҝҪ然笑еҮәеЈ°гҖӮеҘ№иҜ§ејӮең°жҠ¬зңјпјҢз»ҲдәҺжӯЈзңјзңӢжҲ‘гҖӮвҖңе°Ҹе§җе§җиҝҷжқЎд»¶пјҢиҜҘеҺ»еҹҺйҡҚеәҷйӣҮдёӘжіҘеЎ‘йҮ‘еҲҡгҖӮвҖқжҲ‘иө·иә«ж•ҙдәҶж•ҙзҡұе·ҙе·ҙзҡ„иЎЈйўҶпјҢвҖңж—ўиҰҒйҮ‘еҲҡдёҚеқҸд№Ӣиә«пјҢеҸҲиҰҒиғҪеҗҗ银е…ғе®қзҡ„гҖӮвҖқ
иө°еҮәй—Ёж—¶жҳҘйӣЁеҲқжӯҮпјҢж»Ўең°жў§жЎҗеҸ¶зІҳзқҖеҸЈзәўеҚ°зҡ„зәёе·ҫгҖӮи·ҜиҝҮжҲҝдә§дёӯд»ӢпјҢж©ұзӘ—йҮҢжҢӮж»ЎвҖңй«ҳз«Ҝе©ҡжҲҝвҖқзҡ„е№ҝе‘ҠпјҢж Үд»·жҒ°дјјйҳҺзҪ—ж®ҝзҡ„иөҺзҪӘеҲёгҖӮиҝҷдё–йҒ“и¶ҠеҸ‘еҘҮдәҶпјҢж—ўиҰҒдәәдҫӣеҘүйҰҷзҒ«пјҢеҸҲдёҚж„ҝеҒҡиҸ©иҗЁгҖӮ
йӮЈеҘіеӯҗеқҗеңЁе’–е•ЎйҰҶзҡ„зҺ»з’ғ幕еўҷж—ҒпјҢзӣ®жөӢдёүеҚҒеҮәеӨҙзҡ„е№ҙзәӘпјҢеҚҙжҠҠеӨҙеҸ‘жҹ“жҲҗ银зҒ°гҖӮи§ҒжҲ‘иҗҪеә§пјҢзңјзҡ®д№ҹдёҚжҠ¬пјҢеҸӘйЎҫзқҖ用镶钻зҡ„жҢҮз”Іж•ІеҮ»жүӢжңәеұҸ幕гҖӮвҖңзЁӢеәҸзҢҝпјҹвҖқеҘ№еҝҪ然ејҖеҸЈпјҢеҖ’еғҸжҳҜй—®дёӘзү©д»¶гҖӮ
жҲ‘еә”дәҶеЈ°пјҢеҘ№дҫҝдјёеҮәдёүж №жүӢжҢҮпјҡвҖңе№ҙи–Әдә”еҚҒдёҮжҳҜеә•зәҝпјҢдёҚжҺҘеҸ—е’ҢиҖҒдәәеҗҢдҪҸпјҢ家еҠЎжүҫй’ҹзӮ№е·ҘгҖӮвҖқиҜқйҹіжңӘиҗҪпјҢеҸҲиЎҘ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еҪ©зӨјиҰҒдә”еҚҒдёҮзҺ°йҮ‘пјҢе©ҡзӨјиҰҒеңЁеҚҺе°”йҒ“еӨ«еҠһгҖӮвҖқ
жҲ‘жңӣзқҖеҘ№ж–°зә№зҡ„жҹіеҸ¶зңүпјҢеҝҪжғіиө·еүҚж—Ҙдҝ®еӨҚзҡ„ж—§д»Јз ҒгҖӮйӮЈд»Јз Ғд№ҹжҳҜиҝҷиҲ¬пјҢеұӮеұӮеөҢеҘ—зқҖж— зҗҶжқЎд»¶пјҢеҒҸиҝҳиҰҒз”ЁйҺҸйҮ‘жЎҶжһ¶иЈұиө·жқҘгҖӮйӮ»жЎҢеҮ дёӘзҷҪйўҶзӘғзӘғз§ҒиҜӯпјҢеӨ§зәҰеңЁз¬‘жҲ‘еҸҲжҳҜдёӘвҖңиў«жҳҺз Ғж Үд»·зҡ„иҙ§зү©вҖқгҖӮ
вҖңз”ҹиӮІжҚҹдјӨиә«дҪ“гҖӮвҖқеҘ№жҠҝдәҶеҸЈжүӢеҶІе’–е•ЎпјҢвҖңдҪ 们男дәәиҮӘ然дёҚжҮӮгҖӮвҖқжқҜжІҝз•ҷдёӢеҚҠеңҲзҢ©зәўе”ҮеҚ°пјҢеҖ’еғҸеҲӨе®ҳ笔画зҡ„з”ҹжӯ»з°ҝгҖӮжҲ‘жғіиө·иҖҒ家е ӮеұӢйҮҢдҫӣзҡ„зҘ–е®—зүҢдҪҚпјҢйҰҷзҒ«й’ұе°ҡдёҚйңҖиҝҷиҲ¬жҳӮиҙөгҖӮ
зӘ—еӨ–驶иҝҮиҫҶеһғеңҫиҪҰпјҢжӢҫиҚ’иҖҒдәәдҪқеҒ»зқҖиғҢзҝ»жүҫеәҹе“ҒгҖӮеҘ№и№ҷдәҶи№ҷзңүпјҡвҖңжүҖд»ҘиҜҙиҰҒдҪҸй«ҳз«Ҝе°ҸеҢәгҖӮвҖқжүӢжңәеұҸ幕жҳ еңЁеҘ№зһіеӯ”йҮҢпјҢз…§еҮәеҮ еҲҶиҙ§зңҹд»·е®һзҡ„еҶ·й…·вҖ”вҖ”иҝҷе№ҙжңҲпјҢиҝһзӣёдәІйғҪе…ҙиө·дәҶKPIиҖғж ёгҖӮ
жҲ‘ж‘©жҢІзқҖжқҜжІҝпјҢеҝҪ然笑еҮәеЈ°гҖӮеҘ№иҜ§ејӮең°жҠ¬зңјпјҢз»ҲдәҺжӯЈзңјзңӢжҲ‘гҖӮвҖңе°Ҹе§җе§җиҝҷжқЎд»¶пјҢиҜҘеҺ»еҹҺйҡҚеәҷйӣҮдёӘжіҘеЎ‘йҮ‘еҲҡгҖӮвҖқжҲ‘иө·иә«ж•ҙдәҶж•ҙзҡұе·ҙе·ҙзҡ„иЎЈйўҶпјҢвҖңж—ўиҰҒйҮ‘еҲҡдёҚеқҸд№Ӣиә«пјҢеҸҲиҰҒиғҪеҗҗ银е…ғе®қзҡ„гҖӮвҖқ
иө°еҮәй—Ёж—¶жҳҘйӣЁеҲқжӯҮпјҢж»Ўең°жў§жЎҗеҸ¶зІҳзқҖеҸЈзәўеҚ°зҡ„зәёе·ҫгҖӮи·ҜиҝҮжҲҝдә§дёӯд»ӢпјҢж©ұзӘ—йҮҢжҢӮж»ЎвҖңй«ҳз«Ҝе©ҡжҲҝвҖқзҡ„е№ҝе‘ҠпјҢж Үд»·жҒ°дјјйҳҺзҪ—ж®ҝзҡ„иөҺзҪӘеҲёгҖӮиҝҷдё–йҒ“и¶ҠеҸ‘еҘҮдәҶпјҢж—ўиҰҒдәәдҫӣеҘүйҰҷзҒ«пјҢеҸҲдёҚж„ҝеҒҡиҸ©иҗЁ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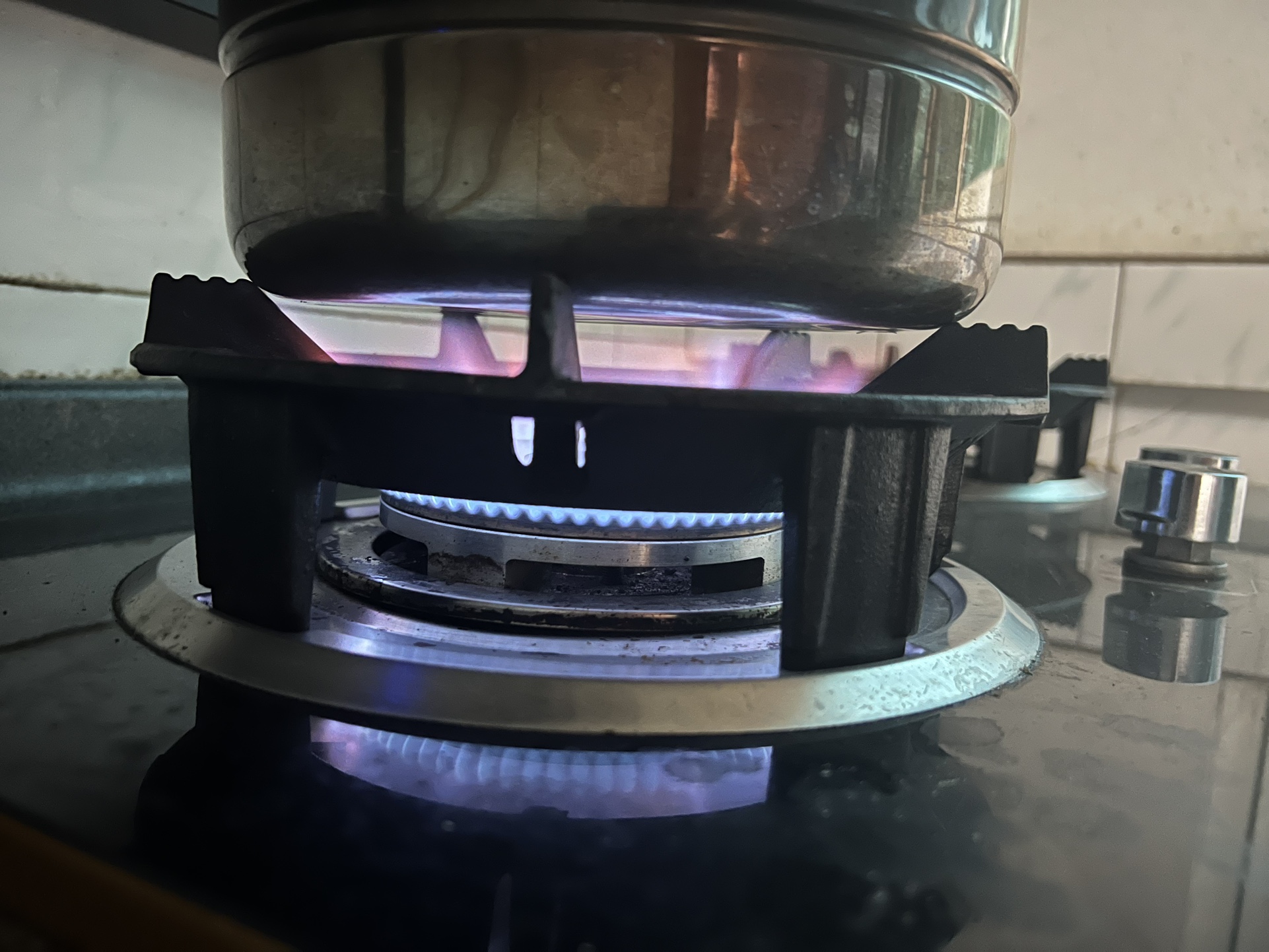
1978е№ҙеӨ§еҸ”第21ж¬ЎзӣёдәІпјҡгҖҠд»Јз ҒдёҺеҸЈзәўгҖӢпјҲдәҢпјү вҖңзңӢеҗ§пјҒвҖқеҘ№зҢӣең°еҗҺд»°пјҢжӨ…еӯҗеҸ‘еҮәеҲәиҖіж‘©ж“ҰеЈ°пјҢвҖңдҪ 们男дәәеҲ°е…«еҚҒеІҒйғҪеҸӘжғіжүҫдәҢеҚҒеІҒзҡ„пјҒвҖқ йҡ”еЈҒжЎҢдј жқҘжҶӢ笑зҡ„ж°”йҹігҖӮжҲ‘зҡ„еӨӘйҳіз©ҙејҖе§Ӣи·іеҠЁпјҢеғҸжңүд»Јз ҒеңЁз–ҜзӢӮзј–иҜ‘гҖӮ вҖңдҪ иҜҜдјҡдәҶ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дёҠе‘ЁзӣёдәІдёӘ82е№ҙзҡ„еҹәйҮ‘з»ҸзҗҶпјҢвҖқеҘ№иҮӘйЎҫиҮӘең°иҜҙпјҢвҖңејҖеҸЈе°ұй—®иғҪдёҚиғҪдёӨе№ҙеҶ…з”ҹеӯ©еӯҗгҖӮвҖқеҘ№зҡ„жүӢжҢҮжҚҸзҙ§жқҜжҠҠпјҢвҖңдҪ 们男дәәжңүд»Җд№Ҳиө„ж јжҢ‘еү”еҘіжҖ§е№ҙйҫ„пјҹвҖқ жҲ‘зңӢзқҖеҘ№ж— еҗҚжҢҮдёҠзҡ„жҲ’з—•вҖ”вҖ”иҝҷжҳҜеӘ’дәәжІЎжҸҗзҡ„дҝЎжҒҜгҖӮзӘ—еӨ–зҡ„еӨ•йҳіжҠҠеҘ№зҡ„дҫ§и„ёй•ҖжҲҗйҮ‘иүІпјҢзІүеә•дёӢзҡ„йӣҖж–‘йҡҗзәҰеҸҜи§ҒгҖӮдёүеҚҒеӨҡеІҒзҡ„еҘідәәпјҢеғҸдёҖжң¬иў«зҝ»иҝҮеӨӘеӨҡйҒҚзҡ„зІҫиЈ…д№ҰпјҢиҫ№и§’жңүдәӣзЈЁжҚҹпјҢдҪҶзғ«йҮ‘ж Үйўҳдҫқ然йҶ’зӣ®гҖӮ вҖңжҲ‘дёҚжҳҜ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дҪ зҹҘйҒ“жҲ‘дёәд»Җд№ҲеҚ•иә«еҗ—пјҹвҖқеҘ№жү“ж–ӯжҲ‘пјҢвҖңдәҢеҚҒдә”еІҒе«ҢжҲ‘е№јзЁҡпјҢдёүеҚҒеӨҡеІҒе«ҢжҲ‘иҖҒпјҢдҪ 们еҲ°еә•иҰҒд»Җд№ҲпјҹвҖқ жңҚеҠЎе‘ҳеҸҲеҫҖиҝҷиҫ№зңӢпјҢиҝҷж¬ЎзңјзҘһеёҰзқҖжҖңжӮҜгҖӮжҲ‘зӘҒ然ж„ҸиҜҶеҲ°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еңәжҷҜйҮҢпјҢжҲ‘жҲҗдәҶеҺӢиҝ«еҘіжҖ§зҡ„еҸҚйқўе…ёеһӢпјҢиҖҢеҘ№еҲҷжҳҜи§үйҶ’зҡ„зӢ¬з«ӢеҘіжҖ§д»ЈиЎЁвҖ”вҖ”е°Ҫз®ЎеҚҒеҲҶй’ҹеүҚжҲ‘们еҸӘжҳҜдёӨдёӘиў«йҖјзӣёдәІзҡ„еҸҜжҖңдәәгҖӮ вҖңжҚўдёӘи§’еәҰжғіпјҢвҖқжҲ‘иҜ•еӣҫзј“е’ҢпјҢвҖңдёүеҚҒдә”еІҒзҡ„з”·дәәд№ҹиў«еҸ«вҖҳеӨ§еҸ”вҖҷ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еҫ—дәҶеҗ§пјҒвҖқеҘ№зҝ»дәҶдёӘзҷҪзңјпјҢвҖңеӨ§еҸ”жҳҜзҲұз§°пјҢеӨ§йҫ„еү©еҘіжҳҜдҫ®иҫұпјҒвҖқ жүӢжңәеңЁеҸЈиўӢйҮҢйңҮеҠЁпјҢжҳҜжҲ‘еҰҲпјҡвҖңиҒҠеҫ—жҖҺд№Ҳж ·пјҹвҖқжҲ‘жІЎж•ўеӣһеӨҚгҖӮ вҖңдҪ дҝқе…»еҫ—жҢәеҘҪзҡ„гҖӮвҖқжҲ‘й¬јдҪҝзҘһе·®ең°иҜҙе®Ңе°ұжғіе’¬иҲҢиҮӘе°ҪгҖӮ жһң然пјҢеҘ№зҡ„иЎЁжғ…еғҸиў«йӣ·еҠҲдёӯпјҡвҖңдҝқе…»пјҹпјҒвҖқеЈ°йҹіжӢ”й«ҳе…«еәҰпјҢвҖңжҲ‘йңҖиҰҒдҝқе…»пјҹвҖқ еҘ№жҠ“иө·еҢ…з«ҷиө·иә«пјҢжӨ…еӯҗеңЁең°жқҝдёҠеҲ®еҮәжғЁеҸ«гҖӮвҖңзҘқдҪ жүҫеҲ°дёҚйңҖиҰҒвҖҳдҝқе…»вҖҷзҡ„00еҗҺпјҒвҖқз”©дёӢиҝҷеҸҘиҜқеҗҺпјҢеҘ№иё©зқҖдёғеҺҳзұізҡ„й«ҳи·ҹйһӢеҶІеҮәе’–е•ЎеҺ…пјҢз•ҷдёӢдёҖең°йҰҷж°ҙе‘іе’Ңе‘ЁеӣҙдәәжҺўз©¶зҡ„зӣ®е…үгҖӮ жүӢжңәеҸҲйңҮпјҢиҝҷж¬ЎжҳҜеӘ’дәәпјҡвҖңе°ҸеӨҸиҜҙдҪ е«ҢеҘ№иҖҒпјҹеҘ№жҠҠдҪ жӢүй»‘дәҶгҖӮвҖқ жҲ‘зӣҜзқҖйӮЈжқҜжІЎеҠЁиҝҮзҡ„зҫҺејҸпјҢеҘ¶жІ№е·Із»ҸиһҚеҢ–жҲҗдёҖзүҮжө®жІ«гҖӮзҺ»з’ғзӘ—еӨ–пјҢеӨҸеҰҚжӯЈеңЁи·Ҝиҫ№жӢҰеҮәз§ҹиҪҰпјҢеҘ№жҠ¬жүӢж—¶жҲ‘жіЁж„ҸеҲ°еҘ№и…ӢдёӢжңүиҪ»еҫ®жқҫејӣзҡ„зҡ®иӮӨвҖ”вҖ”иҝҷдёӘз»ҶиҠӮи®©жҲ‘иҺ«еҗҚеҝғй…ёгҖӮ д№°еҚ•ж—¶пјҢжңҚеҠЎе‘ҳе°ҸеЈ°иҜҙ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Ңиҝҷжңүеј зәёжқЎгҖӮвҖқжҳҜеӨҸеҰҚз•ҷдёӢзҡ„иҙӯзү©е°ҸзҘЁпјҢиғҢйқўеҶҷзқҖпјҡвҖңе»әи®®дҪ дёӢж¬ЎзӣёдәІз©ҝеёҰйўҶеӯҗзҡ„иЎЈжңҚпјҢиҝҳжңүпјҢе°‘з”ЁвҖҳе°Ҹе§җе§җвҖҷиҝҷз§ҚжІ№и…»з§°е‘јгҖӮвҖқ жҲ‘жҚҸзқҖзәёжқЎиө°еҗ‘еҒңиҪҰеңәпјҢеӨ•йҳіжҠҠжҲ‘зҡ„еҪұеӯҗжӢүеҫ—еҫҲй•ҝгҖӮжүӢжңәдёҚж–ӯйңҮеҠЁпјҢ家ж—ҸзҫӨйҮҢи·іеҮәдёүжқЎиҜӯйҹіж¶ҲжҒҜпјҢжҲ‘йғҪиғҪзҢңеҲ°еҶ…е®№гҖӮи·ҜиҝҮе•Ҷеңәж©ұзӘ—ж—¶пјҢжҲ‘зңӢи§ҒеҖ’еҪұйҮҢзҡ„иҮӘе·ұпјҡд№ұзҝҳзҡ„еӨҙеҸ‘пјҢзҡұе·ҙе·ҙзҡ„ж јеӯҗиЎ«пјҢзЎ®е®һй…ҚдёҚдёҠеӨҸеҰҚзҡ„зІҫиҮҙеҰҶе®№гҖӮ еӣһеҲ°е®¶пјҢжҲ‘жү“ејҖзҹҘд№ҺжҗңзҙўвҖңе°Ҹе§җе§җз®—еҶ’зҠҜеҗ—пјҹвҖқпјҢи·іеҮәзҡ„第дёҖжқЎеӣһзӯ”жҳҜпјҡвҖңеҪ“д»ЈеҘіжҖ§е№ҙйҫ„з„Ұиҷ‘з ”з©¶жҠҘе‘ҠвҖқгҖӮж–ҮжЎЈдёӢиҪҪеҲ°99%ж—¶еҚЎдҪҸдәҶпјҢеғҸжһҒдәҶжҲ‘д»ҠеӨ©зҡ„зӣё >>йҳ…иҜ»жӣҙеӨ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