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壳怀表的指针开始逆旋。我数着齿轮的喘息,看黄铜表链在腕上勒出1874年的勒痕。阁楼东南角的威尼斯镜蒙着海盐。每当涨潮时分,镜面就会渗出蛋白照片特有的棕褐色,像一块正在显影的巨型相纸。 衣橱最深处挂着件蛀空的燕尾服。月光好的夜晚,金线刺绣的常春藤会从袖口爬出,沿着橡木地板生长,藤蔓末端结着微型铜齿轮。这些金属果实总在黎明前氧化成灰,灰烬里浮出同一串花体数字:1874.07.23。 留声机又开始自鸣。铜绿在唱片沟槽里生根,指针划出的音符充满了铁锈的味道。划过虫蛀的贝多芬乐章时,铜喇叭口吐出带霉味的舞会请柬。那些烫金字母在落地瞬间褪成我的笔迹,日期栏永远洇着一团墨渍,像是拒绝愈合的伤口。 暗房的红灯下,显影液突然沸腾。蛋白相纸在托盘里蜷缩又舒展,最终浮现的并非伦敦街景,而是一面布满裂痕的威尼斯镜。镜中男人背对镜头,深蓝燕尾服后摆缀满铜绿,左手悬在半空,像是要抓住某根不存在的怀表链。 我触摸相纸的刹那,左腕传来金属灼烧的剧痛。怀表弹开的壳内壁结着盐霜,罗马数字Ⅸ的阴影里蜷缩着一朵锡箔玫瑰。她跟我昨夜从衣橱地板上扫起的残花拥有相同的腐烂角度。 书房抽屉开始自动生产褪色的诗稿。羽毛笔用我的血调制墨水,在羊皮纸上书写倒置的十四行诗。透过放大镜,那些反写的句子显影成同一段独白: "我向虚空伸出右手,只为接住自己左手递来的枯萎。" 月圆时,阁楼的镜面会涨潮。咸涩的雾气从裂缝渗出,在地毯上勾勒出华尔兹的鞋印。我跟着不存在的舞曲旋转,直到所有蜡烛同时淌下鲸脂。烛泪凝固的瞬间,镜中映出我右肩的褶皱——与蛋白照片里男人燕尾服的扭曲纹路完美重合。 怀表停摆后成了沙漏。铜绿从表链向静脉蔓延,每次心跳都震落年代的细碎。表皮脱落后,我看见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显影液混合香槟的棕褐色浆液。它们冲刷着肋骨的银盐颗粒,冲刷出另一具半透明的躯体。 某场暴雨后,威尼斯镜彻底雾化成相纸质地。我用指甲刮开表面乳剂层,刮出无数个同心圆年轮。最深处埋着一枚铜钮扣,背面蚀刻的指纹在显微镜下分裂成两枚:一枚属于1874年的氧化银,一枚属于此刻正在溃烂的角质层。 衣橱里的常春藤开花了。蓝玫瑰从袖口血丝绒中钻出,花瓣背面印着褪色的舞步图解。我按图示旋转,皮鞋跟在大理石上敲出摩尔斯电码的节奏。电码内容非常简单——“你,就是他。” 留声机突然吞下自己的音符。唱片在寂静中裂成碎片片,每一片都映着不同角度的威尼斯镜,镜中人的左手始终虚握,等待某个永远不会交握的右手完成这个世纪的邀舞。 怀表在正午炸成一捧铜绿灰烬。灰雾中升起新的威尼斯镜框,框内裱着1874年未显影的相纸。我站进画幅右侧空位时,听见暗房传来显影液翻涌的潮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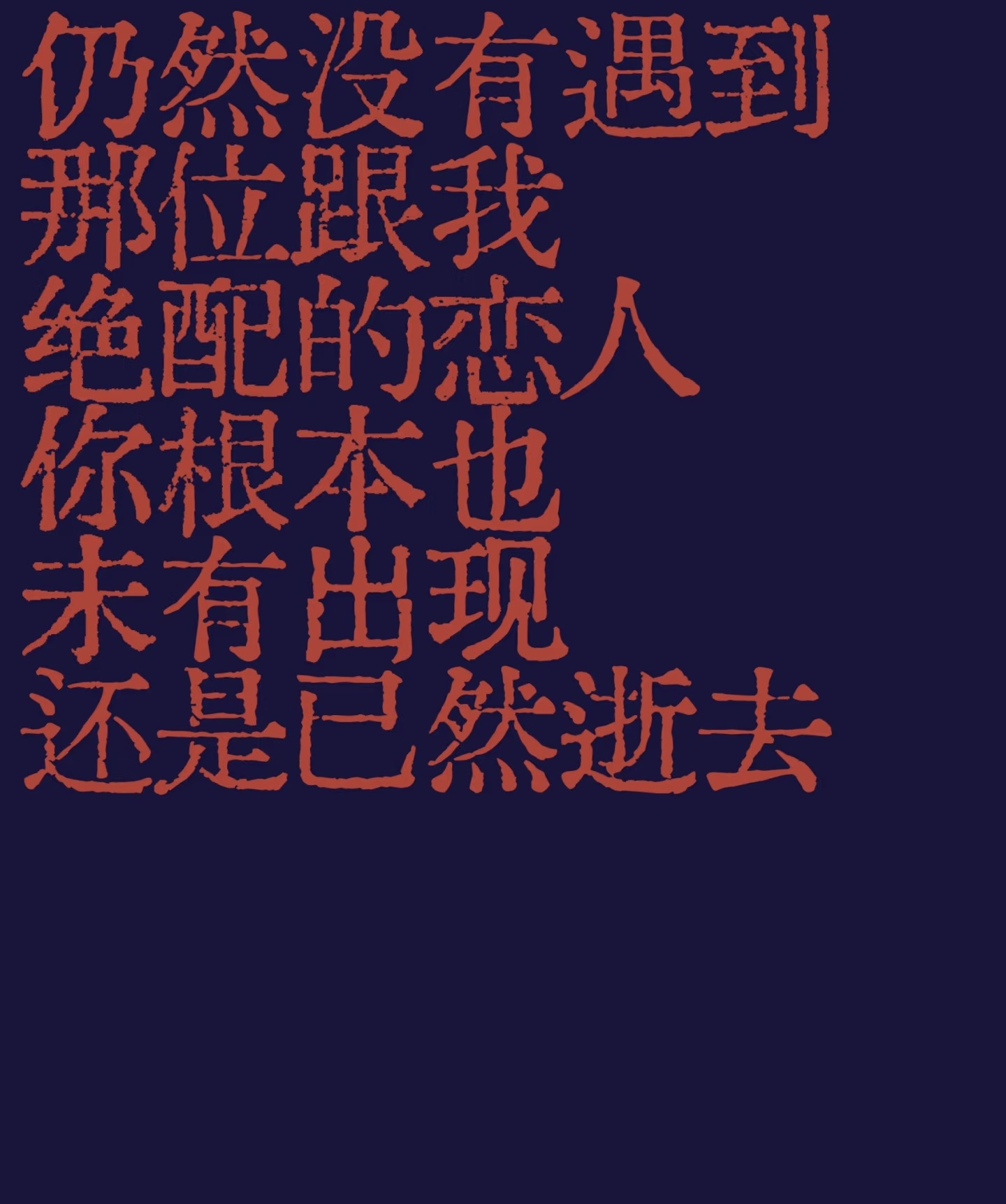
评论:
Souler: 等我想想怎么把你的手和脑子偷过来[愤怒]你这个可恶的令人嫉妒的家伙
一点都不可爱: 把他骗回家就可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