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柳永《菊花新》说去
昨夜偶翻柳永词,顺手翻到《菊花新》,竟瞅了两眼。不知怎的,这把年纪倒读得进柳永词了,前些日读起来几首竟也儿女情长的泪眼。大约是从前少年个性,热血满盈、只有那金戈铁马、挥斥方遒,不屑于花前月下、凝眸蹙眉。
直观这词起来,倒是一副少年云雨前后的直白,这在古人正文间很是难得,难怪赏析里清代腐儒点评世间第一等淫词。
少年期间,最恨腐儒,那倒是一套道貌岸然,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伎俩。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些当时的意见领袖道德绑架下,面对男欢女爱时总是犹抱琵芭半遮面。近现代文学,似乎学了西方开放的皮,凡书总要沾点性,却像是生生的硬硬的拉扯进来、没有骨子里的自然。所以看起来这首词,真的是自然天成,也无怪乎柳三变。
男欢女爱这事,本是饮食男女常识,可成了中国文学禁忌。可笑的是你要连这点事都说不明白,都不敢说,都要包装伪装,指望你的文字下面隐藏的思想能有多全面?王阳明在对朱熹“去人欲、存天理”重构说的很明白,这个人欲不是说“人的欲望”、而是说“人的枷锁”,这个枷锁是别人告诉你的规范、而不是你自己的自觉认知,你求真理,你的要去格物博约、让自己认知“天理”。
男欢女爱,本来就是人的属性,也讲个自然天成。欢爱的基础由自身认知决定,兽的欢爱是基因筛选,人的欢爱是认知筛选,这个认知筛选也能区分出人性与兽性。如词,竟是爱了、睡了,完了意犹未尽、还要默默看,它这场景全一副欢好之美。非得说个劳什子淫,只能说自己心中是魔、这世间自然是魔界。
《白鹿原》嘉轩媳妇仙草,扯了桃木小棒槌、掀了肚兜,是自然;田小娥尿了鹿子林一脸,是反抗。最是可怜鹿兆鹏媳妇、冷先生女儿,却是婚后多年未经男女,落了个神经错乱、被冷先生一副药药死,然后还落了个淫病致死的冷语。可笑的是,乡里乡外村村有私生子的鹿子林,可以拿着垫了草的饭内涵兆鹏媳妇是畜生,活脱脱一个人面兽心。
这大同世界里,各色的人儿、都在床底事上诞生,都向往着这床底事儿,却都把自己的“欲”加在这本真的事上,有多少是男版女版鹿子林?又有多少床底事,如《菊花新》般的本真?不妨睡前睡后都挺美,其他的,何必呢?活在当下,你们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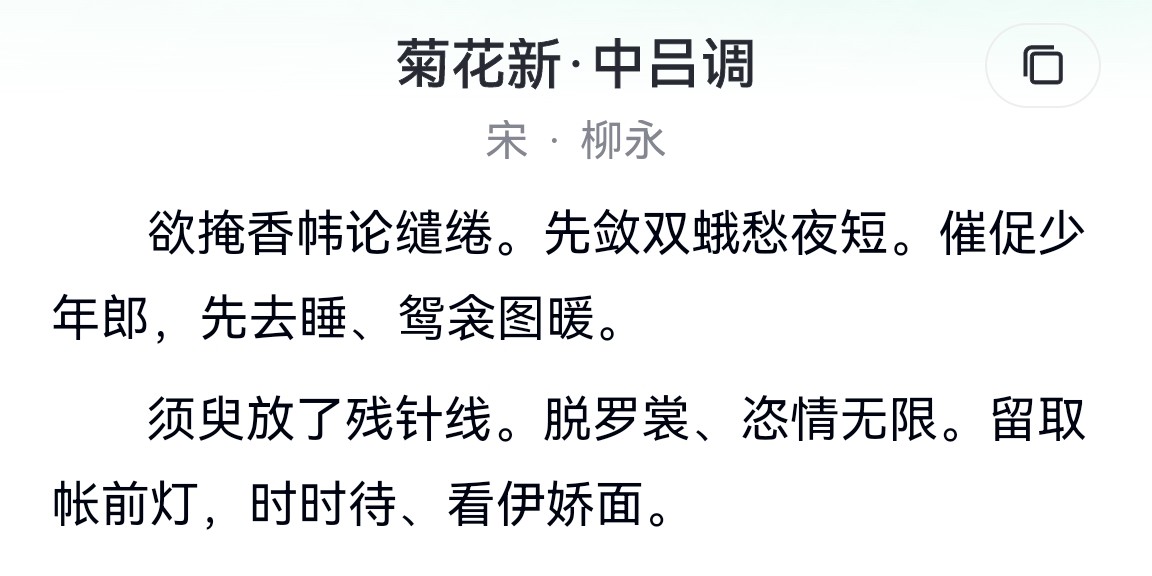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