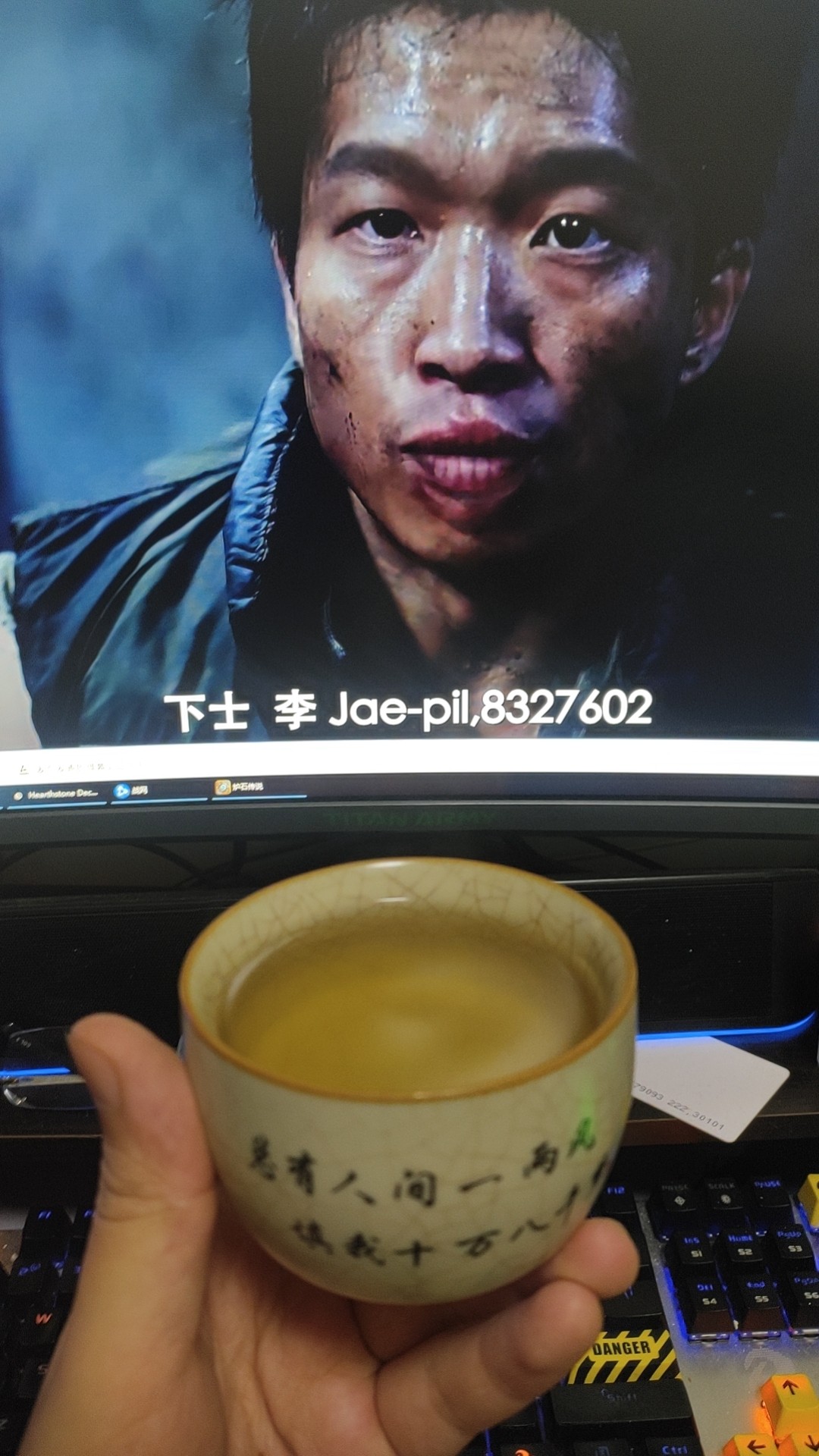近些年“情绪价值”这个词被反复提及 ,好像一旦这个人被发现不能给人“情绪价值”,身边的朋友都要赶紧远离他,不屑为伍。
小说《围城》里有一幕,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方鸿渐失恋后悲痛难当,便约好友喝酒解闷。但他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安慰,反而遭好友一顿嘲讽:“为一个黄毛丫头就那么愤世嫉俗,真是小题大做。”
方鸿渐起初感到惊讶,继而愤怒,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汪曾祺回忆录》有这样一个人物——二愣子。
二愣子是阜平人,虽然只是文工团的一个小杂工,但几乎团里所有人,都对他“印象深刻”。
因为他有个很明显特点:爱诉苦。
1937年,日本兵在阜平烧杀掳抢,他的父母被杀害,妹妹被糟蹋。
残酷的打击,直接把他击落至深渊。
在一次大会上,他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说着说着就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很多人见了为之动容,纷纷送来安慰和鼓励。
可后来每次见面,他都要倾诉一番,每次都要哭得撕心裂肺。
那些曾经安慰过他的人,早已听烦,开始说他晦气,到最后,甚至干脆不理,见他就躲着走。
试想,谁愿意让一个情绪黑洞天天撕扯自己的能量呢?
生活不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烦闷。
一遭遇痛苦就想从别人那获取安慰,时间久之,别人自然会反感和厌恶。
别人的情绪价值终究是有限的,没人会一直支撑你。
试图从别人那索取情绪安慰,换来的多半是敷衍与不解。情绪价值从来不是依靠别人提供的,首先你要自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成年人的世界,悲喜自渡,苦乐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