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还休、点到为止 我生活在没有电影院的小镇上,极少进电影院。对电影院的深刻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偶尔学校会组织去看一些需要写观后感的电影,每次看这种电影我能从父母那里要来5毛钱,买一小包用作业本纸张裹成圆锥形的瓜子,在电影院里边吃瓜子边看着荧幕上的不知所云,最后回家写一篇连正反派都分不清的所谓观后感。后来陪朋友看《速度与激情》我能睡着,陪孩子看《铃芽之旅》我能睡着,成年后唯一进电影院不犯困的经历是2005年陪别人家媳妇儿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至于为什么没睡着,只能说肯定与电影无关。总结下来电影院是我这个农村人配不上的娱乐形式。 这部《好东西》在2024年底实在太火,社交平台的信息流里不停能刷到相关内容,订阅的微信公众号里也能看到热议文章,却一点也挑不动我的好奇心,直到前些天听某个“不明白”推荐了这部电影,她的原话是:“你看一看这里面的人,他们都是现代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地让这些现代人完全听“他”的话呢?”,就这一句让我决定要看看这部电影。这两天忙里偷闲以1.5倍速的方式,反复把这部电影看了两遍,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它是一部欲说还休、点到为止的擦边电影。 从铁梅的职业说起:“调查记者”,但凡关注过历年来热门新闻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职业的沉重分量。从三聚氰胺奶粉到地沟油,从煤矿事故到环境污染,这群人始终冒着危险站在新闻第一线去发掘与每个人的安全、健康息息相关的幕后真相。引用公众号文章里的数据:“2011年,传播学者张志安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当年他联系到了334名调查记者。2017年,张志安在撰写《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只能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2018年,张志安估算在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不过数十人。”这个职业的从业人数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在2024年的食用油报道中,新京报的记者再次引起了大家对调查记者这一职业的关注,微博网友们发起了给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打赏的活动,我特意下载微博去响应了打赏活动。在电影里铁梅的同事问她为什么放弃做调查记者,铁梅简单的答了一句:“因为我懦弱”,从这一句欲说还休的解释,让我们可以想象做调查记者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面对怎样的风险。没有人有权力要求别人去为自己勇敢,这部电影不需要深入的讨论什么,只是提起,就足以让我们怀念和铭记那些新闻真相背后的无名英雄。 故事的背景是在上海,这个城市因为2022年的某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Cosplay节,让我在心里把它视作了全国最具现代文明气息的都市,这也是一个对疫情留有惨痛记忆的城市。铁梅第一次去小叶家的时候,惊叹于小叶在家里种植的各种蔬菜。小叶说自己根本不做饭,随后向铁梅展示了客厅里储存的各种食物,架子上堆满了盒装即食食物、角落里成箱的酒水饮料,铁梅认为吃不完,小叶说早晚能用上。对这一段场景想起什么了吗?作为一个农村人,疫情期间我并没有亲历过物资缺乏,但我对那段时期有着无需亲历也能共情的深刻记忆。而那些真正亲历过的人们,他们最终会把这段记忆留在生活方式里,刻在基因里。导演不愿忘却,但也只能点到为止。 有人说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除了电影里男性角色嘴里蹦出来的女权主义名词、服饰上的一些自我肯定(铁梅沙发上的衣服印着YES,I'M A FEMINTST)、自我接纳(铁梅和小马一起做饭的时候穿的衣服印着"If you see apples under my t-shirt, it's because I've got them.")的标语,其实整部电影并没有多少女权主义成份。西方世界经历过三波女权主义:第一波在争取选举权、教育权、财产权;第二波在争取性别平等、同工同酬;第三波则在强调多元化、交叉性和性别流动性。前两波女权主义有相关性和延续性,而第三波女权主义对第二波女权主义持批判态度。我们的女权主义其实与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当下的女权主义虽然也有酷儿运动的影子,但更多是在争取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权利。而受西方世界逐渐右倾的影响,简中互联网对女权主义进行了不加区分的污名化,最可怕的是这种污名化与网络暴力的互相助长。铁梅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与同事讨论时,男同事说:“不过骂你的很多都是女的,你以为你在解放女性,人家才不领情。”这句话突出了一个荒诞现象:那些被侵犯权利的人,常常会站在强权一方,冷嘲热讽那些争取权利的人。这种现象正如腰乐队的歌词所唱:“草根是庸俗,很庸俗,说白了就是网民,网民当然是国民,无耻并热闹,是这世上最难唱的一曲悲歌。”如果铁梅在这个场景中穿上那件印着“90%荒诞”的T恤,这将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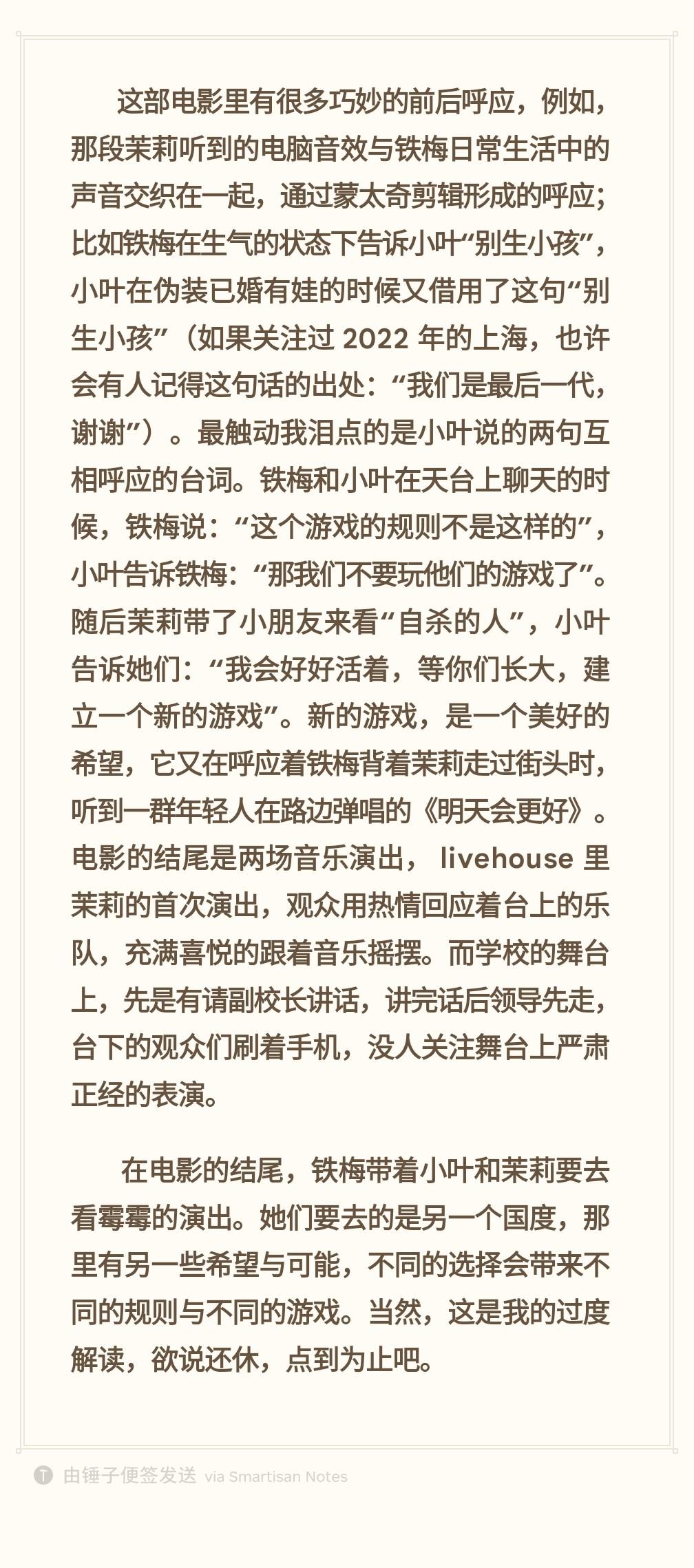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