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个图示不难看出康德的【道德意志】与萨德的【原乐意志】之间的共同结构。两者唯一的差异仅在于,前者贬抑了欲望客体并代之以道德意志,后者则是将欲望客体提升到具有普遍性的地位,主体的意志只能是原乐的意志。……在第一个例子中,快感与惩罚被绑在一起:要爽就得Die,不想Die就没有快感。但在第二个例子中则是快感【或】惩罚之间的选择:得到快感就不必受罚,不然就是维护正义、放弃快感,然后就得接受惩罚。如此,第一个例子实际上并无选择可言,因为那正如拉康举的例子:【要钱或是要命】,无论如何选择都必须失去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拉康称此为【异化】的原因。在第二个例子中才有选择【快感】或【惩罚】的逻辑可能性;也就是选择【善】以维护正义,并因此接受惩罚;或者选择【恶】而作伪证害死无辜者,甚至因此获得他的财产作为奖励。因此,只有在觊觎别人之物这个恶的前提下,才会有康德所谓的善的律法。正如拉康所言:【律法与被抑制的欲望是同一件事,而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发现】。就此而言,道德义务问题的主轴仍然在于原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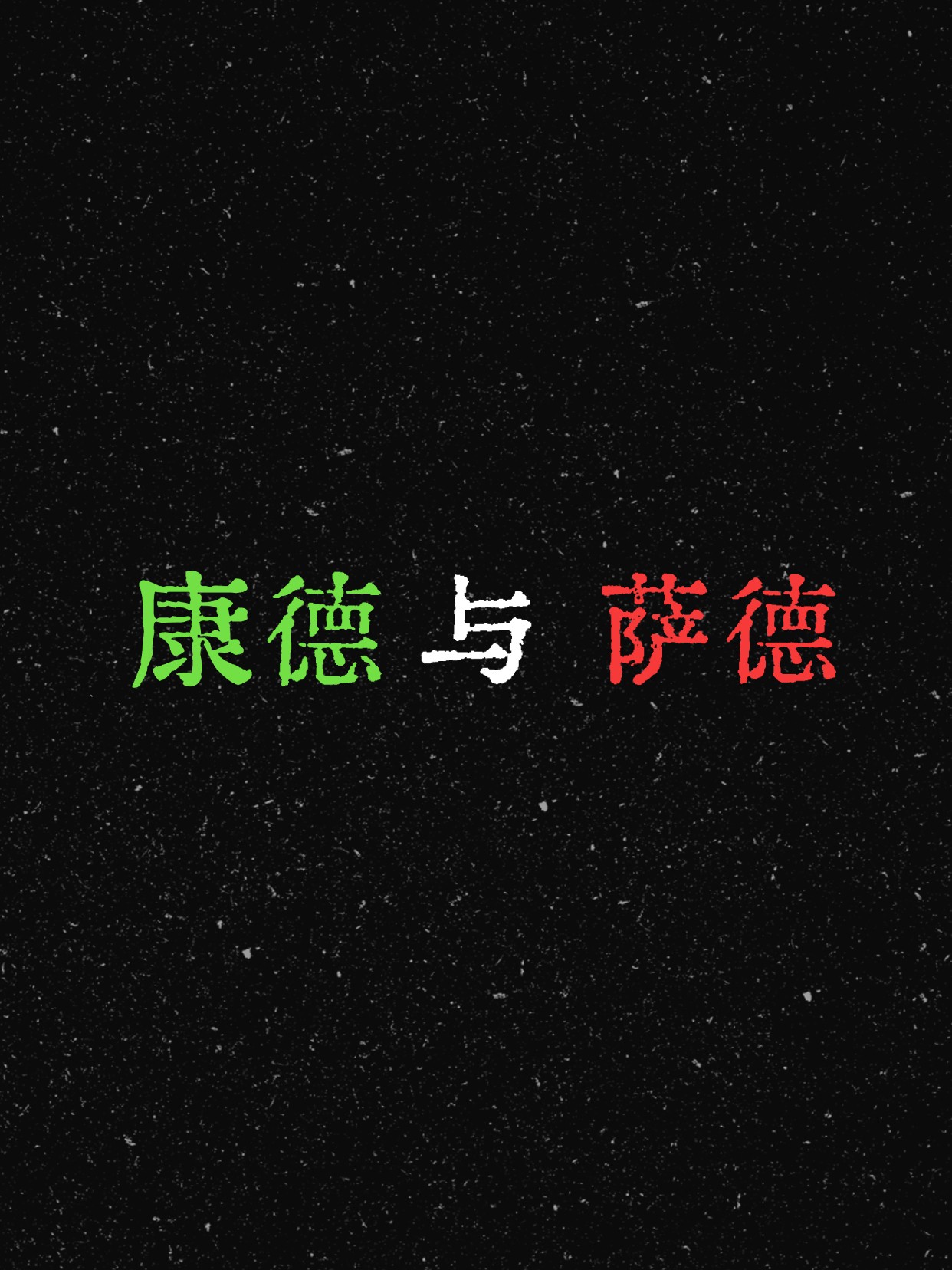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