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高的老冰被不知道几千年的风化压缩成不动的坚岩,连光滑断层都被吹得靛蓝发紫。星夜下的雪曾在千里外地被那么多乡绅喝进旖旎暖酒里,可择克信了他们的邪,竟然自己一头扎了进来。雪被冻成冰,冰被冻成岩,岩石以几百代人沉积的寒威嘲笑着蹬冰靴这一人造物的幼稚。他一脚一脚滑着,每踩上一小块冰头,就有更多的冰谷将他足底向四面八方拉去。泽克咒骂这该死的冰原,可冰原并不反驳,只以风刃与跌破的寒血回应。他左颊被拉开一道豁口,血浆迅速在零下六十度的冷气里发紫发黑,变成小小的黑珍珠粘着在军用口罩上。
后半夜了,可他在天杀的地图标注处兜了许久,连补给基地的影子都没看到,自己反倒迷了路。他的罗盘是严代重工在五年前生产的,家乡的军官们曾说那是集体血与钢铁浇筑的意志,永远不会腐朽。可而今,罗盘在极点附近,还不是摇摇晃晃地打旋儿。他将那罗盘用力地惯到地上,可它除了叮哐了几声,就又在破冰的步伐里静默下去。他的手先是被冻得通红,旋儿风从下摆,衣领,袖口,从四面八方涌进他衣服僵起的小房子,肆意打砸他的温暖记忆。他一开始强自让自己不发抖,而今却不再有力气发抖,在无边无底的寒渊无限期地下坠。红成了紫,紫又成了青蓝苍白的松树色。泽克感受不到伤口的疼痛,也感受不到衣摆的坚硬。他如落幕的国家一样一步步机械地向前走着。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许是过了凌晨罢,太阳浮着烧起来。火红的光晕把冰山顶渲染得如红场上翻滚的尘浪。光爹成海,在极冷的影里跳动着,舞出永世不化的红火。他最后一次回头看向来时的脚印,可除了苍白和银红的平面什么也看不见。忽地,地面似是滚动起来。在他的幻觉里,远丘与近处的平原拉伸,舞动,在地平线上下来回震荡。可他不知道这片冰原已被寒风压实,连雪崩都不会有。滚动的并不是地面,而是他在橙色与白色的天堂里被致盲盲的双眼。他看到大地变成了他早逝的母亲,从下向上站起来,与他的面容愈来愈近,温暖的双手如和风抚过他的面颊。这位铁血军人五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幸福如此触手可及。他的军用背包向下拉扯着,他愤怒地想要将其从身边扔开,可背包和地黏在一起,变得如山般沉重。他翻过身去,被雪地脱去自己的军衣。
红火随着日升褪色,择可的眼里只剩下纯莹白透的清辉。在半个世纪前,北国也曾似雪原一般,以严酷的温暖褪去周遭小国的外衣。它们在血与火里,同他一样对着自己血编织成的黑珍珠久久凝望。他双眼在煦嗳里无神远眺,却只能看到三步之外的地平线。最后一点幸福热泪被冻结,在他眼球上堆成一座晶莹剔透的小坟包。早被同袍清空的补给营地在一里外的低矮山头,像无数个以他骁勇战绩为傲的军官一般,欣慰地望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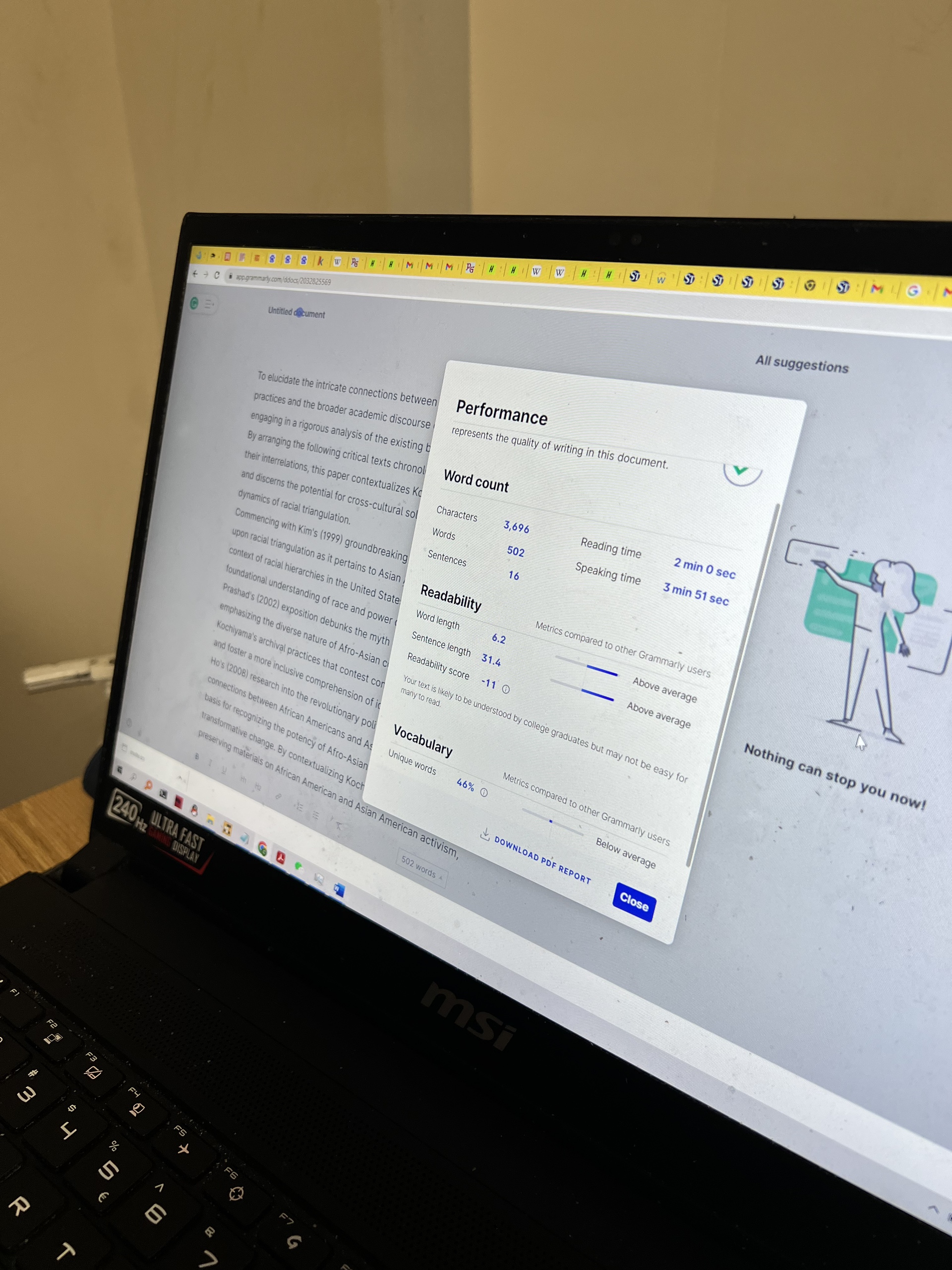
可笑可悲可叹,悬着拙劣的伪装招燕,寄恶俗文心以薄情。
依旧惊叹于乐府诗的巧拙,铸于格律之先,有种文字初生之奥。如果诗是格板,词是沉淀的情感流动郁结的影像,那么乐府可以说兼两者之长时还去除了词忌浅近,诗不跌宕的桎梏。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飰,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这样的文字流,无需分析就能体会到至深之美。
又或者是“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叠字本就难填,五个字去了一个只剩四个了。可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一下子就从动到静,从死到生走了一个轮回。黄昏是死,初是生。奄奄是喧扰,寂寂是无音。死的是喧扰的苦爱求不得,生的是死志久弥新。是而,生起的其实是死志,回光返照,无比决绝,黄昏后寂寂人定都是静字凝魂,旋而“初”是陨凤叫幽谷,碧血玉碎音。叫完了,就该退场了。
似乎在西方也能找到这种存在主义危机浓缩的生死轮回。似伏尔泰的Candide,何塞的悉达多整本书不怎么神迷佶屈,更多的是对自我本存的探索,但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内容对“一切有为法如幻泡影”的回声。或者换成文学分析的说法(当然和对这本书的主流分析其实不太一样…)悉达多对于自我存在的认知不是行为与经历的投影,而是存在的空洞…用人话说就是“你的存在就连自己也没有办法认知,但是在反复求不得怨憎会的痛苦中,你能看到所缺失的东西。而不包含这些缺失的,你所不曾拥有的事物的剪影,就是不净的本我。当你没有缺失,不存在痛苦,也就看不到本我了,升格归化为真我” 真我源于本我之缺,正如骊山的冤魂在自我毁灭中流下铅泪,久别的恋人在凄然殉情里苦求新生而灭寂。

翻译《飞鸟集》[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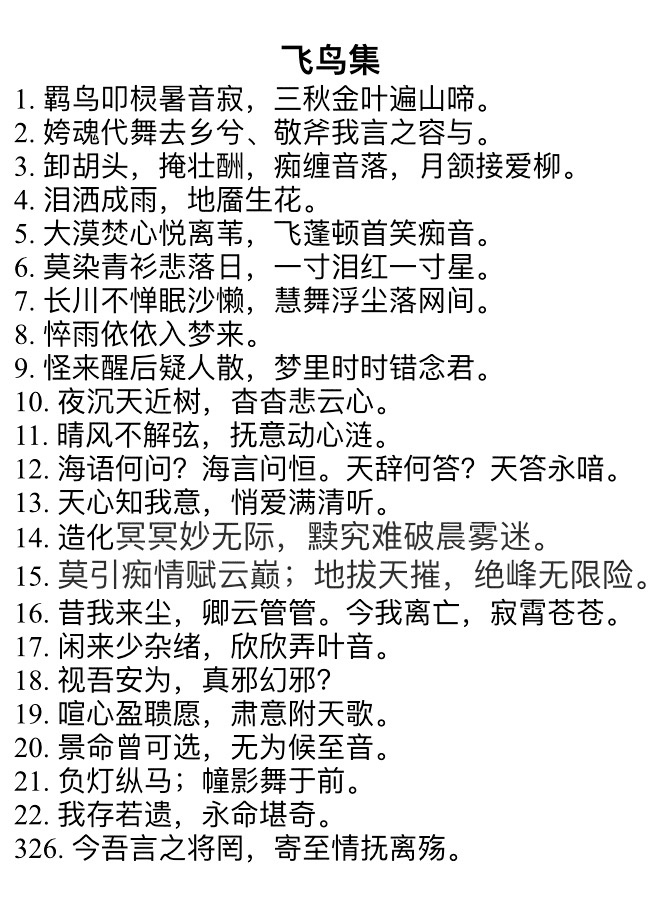
您出生了! >>阅读更多